
首页 > 雪域之子 > 藏韵谈话坊
杨志军:《伏藏》比《达·芬奇密码》饱满
2007年,作家杨志军写完了《藏獒》三部曲。此后,他开始着手写一本叫《伏藏》的悬疑小说,结构类似于《达·芬奇密码》,其写作和修改各花了一年时间。日前,这部70余万字的小说终于与读者见面。作为在青藏高原生活了几十年的杨志军,他的写作根基仍然立足于西藏,不一样的是,新作不再是延续《藏獒》的温情笔调,玩起了悬疑。杨志军试图通过一个看似通俗的故事,去探讨人的精神需求及信仰。在《伏藏》中,对长期备受争议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杨志军认为,他不但不是宗教的叛徒,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
“我注定要用悬疑这种手段来传达我对西藏的认识”
2007年,杨志军到昆明签售《藏獒》,看似平和的他冷不丁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作家没信仰!”三年之后,杨志军出版新作《伏藏》之际,再次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而信仰的问题也再次被提及。杨志军的新书《伏藏》讲述了一个拯救布达拉宫、拯救灵魂信仰的英雄的故事。该书以《达·芬奇密码》的悬疑方式破译神秘的西藏历史、西藏文化和藏教精神,拨开历史迷雾,透视刀光剑影,超越爱恨情仇,以仓央嘉措的情歌为线索,一步步追踪破译出故事的最大悬疑。作家身为佛教信徒,对西藏信仰有着深刻的研究,可以说,这部作品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丰富的关于西藏的小说。
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边巴被杀,引出古老神秘的暗杀组织,中国藏学研究会藏学家香波王子,从北京逃亡到拉萨,从雍和宫追踪到布达拉宫,用仓央嘉措的情歌,在西藏历史和藏地人心的隐秘深处,发掘救世的密钥……雍和宫可以说是《伏藏》一切谜团的开始,也是众人逃亡破译之旅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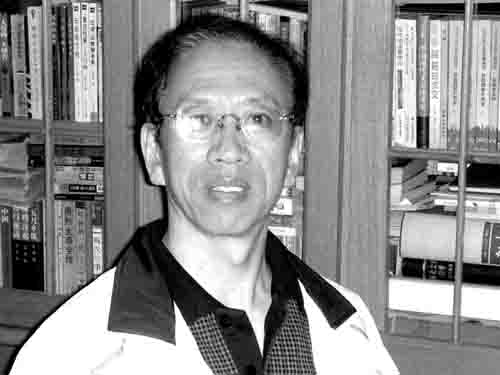
杨志军生于青海,在青藏高原生活了几十年,谈及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他用了一个词:“感恩。”在杨志军的语境里,西藏不仅仅是他生活过的地方,还是一个人和一片土地的缘分。
通常,作家们会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而杨志军在写完《藏獒》三部曲之后,笔锋一转,写起了悬疑小说。谈及创作这部小说最初的构思,杨志军认为:“悬疑只是小说的一种手段。”而通过悬疑这种手段,他同样是在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小说有很多种可能,表达生活也有很多种方法,我之所以选择悬疑,是因为我希望更多的读者能理解我的想法,能传递我内心更多的东西。作家更多的是在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也就是创作动力的来源。”
杨志军在青藏高原生活了四十年,即使是离开以后,他也每年都回去。“这就是我跟青藏高原、跟生活、跟文学的缘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作品是青藏高原的恩赐。我觉得《伏藏》是我命中注定要写的,我注定要选择用悬疑这种手段来传达我对西藏的认识。”
“爱是每个宗教的人和世俗的人都应该面对的”
《伏藏》以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遗言为悬疑目标,用仓央嘉措的情歌为破译密码,完整地呈现出仓央嘉措可歌可泣的一生。仓央嘉措的命运,是小说最揪心、最动容之处。仓央嘉措的情怀,给这部看似充满凶杀恐怖的悬疑小说以圣洁的光辉。
对于仓央嘉措这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伏藏》中,杨志军认为,仓央嘉措不是叛徒,而是宗教改革家。“他是六世达赖,他写了那么多情诗,唱了那么多情歌,爱了那么多姑娘,他是崇尚爱情至上的,他把自己的袈裟甩给自己的师父,说:‘我不要做喇嘛了,我把我受的戒都还给你,我要去做一个自由的人。’于是,他在24岁的时候被处死,他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为了爱,他付出了一切,甚至是生命。”杨志军认为,这是一个古典的悲剧故事,一个莎士比亚式的悲剧,“但是我们了解到这里,往往说他是宗教的叛徒,但我觉得仓央嘉措是一个有志于让宗教由佛性变成人性的伟大的宗教改革家。我为什么要把挖掘《伏藏》的密码用仓央嘉措的情歌来破译呢?因为他本身就代表了西藏精神的一种符号,而这种符号抽象出来很简单,就是爱。”《伏藏》写得非常复杂,但核心就是“爱”。而爱是每个宗教的人和世俗的人都应该面对的,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有爱的个体,同时也应该是一个被爱的个体。
《伏藏》被称为西藏版的《达·芬奇密码》,因为两者的结构颇有相似之处。有人认为这是模仿之作,也有人认为这是致敬之作,甚至是超越之作。对此,喜欢丹·布朗的杨志军在写作时,时刻在回避着《达·芬奇密码》,但是同时杨志军也认为,自己的《伏藏》和《达·芬奇密码》各有千秋,甚至,在某些方面已有所超越。
在杨志军看来,丹·布朗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是破译密码的符号,男女主人公之间几乎没有爱情,没有现实生活中的故事,但“我在《伏藏》里是有现实人物的,用一种司空见惯的三角恋爱,来印证和重现历史上仓央嘉措的爱情。我想用现实来说明历史,又想用历史来说明现实,我一直想把现实和历史交融在一起。这一点是《达·芬奇密码》不具备的,也就是说我笔下的人物是饱满的,有故事的。”
其次,一般来说具有悬疑色彩的小说不可能是悲剧的,不可能有美学意义上和古典意义上的双重悲剧。但《伏藏》中的人物都是悲剧人物。仓央嘉措的历史是悲剧的,现实中的人物也是悲剧的,所有的人物因为爱情付出了生命。爱必须是付出,这种付出甚至是残酷的,我们有时候可能为了爱付出生命,而生命永远值得我们去怀念。这种悲剧丹·布朗是不具备的。“没有这些,我是不敢写的;有了这些,我才相信我的创作是有严肃的主题的,是经过思考的。”杨志军说。
“作家需要冒险和挑战”
“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种报答”

《伏藏》
作者:杨志军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7 月1 日
定价:53元
新报:你说一个人和一个地方有一种缘分,西藏对你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你生活过的地方。你把写作看成是对这片土地的感恩?
杨志军:是,完全是这样。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种报答,这种报答是一个作家必须具有的。这种报答的冲动会激发你的感情,让你的语言变得流畅,让你的思念变得绵长。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作家,我必须激动起来才能写。写长篇花费时间,所以我必须让自己激动的心情有长时间的延续。像我这样的情绪化作家,如果没有对一片土地的深沉的感情,这种情绪是延续不下去的。
新报:写作会对性格产生影响吗?
杨志军:对,要么就说出来,要么就写出来,我选择了后者。我更愿意把你所说的“性格”概括为“天性”,在我的天性里注定要用这种方式完成我对故乡的理解,对西藏精神的理解。我一直说西藏精神,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青藏高原,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被挖掘,还没有在挖掘中感悟到我们内心的需要。西藏是有一种精神的,而我们的旅游、朝拜、阅读,关于西藏的一切,更多人理解的只是表面,而我愿意更深地去发掘。之所以运用悬疑这种手段,是因为这更能便捷地接触到西藏精神的内核。
新报:你谈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你说这部小说对你来说是命中注定的,你好像把写作这件事看得比一般作家更重。
杨志军:写作不是工作,也不是生存方式,而是我生命的需要。我活着就必须这样去表达,去生活,去感恩。小说除了要在生活中获取养分来滋养我们的生命外,我们还要创造。作家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创造一个世界,尽管是虚构的,但它一定是人们需要的。读者和作者都需要一个现实以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能会获得安宁和一种精神的提升。作家对世界的创造,从内心出发,并对生活实现全方位的关照和体验,这是一个作家的本能举动。
“最通俗的手段传达最深刻的思想”
新报:在你的生活中,我相信你并不仅仅在青藏高原生活过,但为什么它让你产生这样深的感情,并感恩地去书写?
杨志军:我出生在青海,我一开始接触的就是西藏文化,青海的大部分土地都是藏区。我和那片土地的关系,除了我生活过、有情感积累外,更多的是一种生命的归属。假如人要分类的话,我自始至终会把自己归为青藏高原这一类。这种归属很奇特,它没有道理可讲,再发达的城市,都会让我感觉到陌生。而青藏高原,哪怕我在这片土地上受尽委屈,它对我也是有恩的。这就是一种生命的皈依吧,如果生命皈依在一片土地上,其实就是皈依在一种信仰上,皈依在一定的精神高度上,因为西藏这片土地是有信仰的。
新报:较之你以前的作品,《伏藏》在写作过程中的挑战体现在哪些地方?
杨志军:首先是悬疑色彩。悬疑是小说的基本手段,很多人都用过,对我的挑战是有这么多悬疑大师了,我还要去“悬疑”,会不会重复?但我必须接受挑战。我必须让这种写作技巧运用得很娴熟,并且有所超越。大师无疑是伟大的,但我们不能回避。我觉得所谓对文学或者对自己的挑战,其实就是对前辈的挑战。
其实,我想用最通俗的手段来传达蕴含着最深刻思想的主题。一般来说,通俗的小说完成的都是通俗的主题,如果主题很深刻、思想很饱满,那你就会发现这部作品是没法看的,不好读。
新报:据我对《伏藏》的阅读体验,它确实读起来像一部通俗小说,是否可以理解为这种通俗是你故意为之?
杨志军:这是我刻意要做的,我必须用最通俗的手段来传达最深刻的思想。很多作品做不到这一点,要么就是主题通俗,要么就是阅读起来感觉晦涩。我想用浅显的手段来包容丰满的思想。这真的是一种挑战,万一我做不好,会让读者认为我在媚俗,放弃了文学的追求和品位。这也是一种冒险,我必须这样去冒险,朝着自己期望达到的高度走下去。我想告诉读者: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缺少什么。
“想通过《伏藏》填补我们的精神空缺”
新报:你在试图给读者轻快的阅读感,而非晦涩难懂。
杨志军:但你阅读完以后会发现,这不仅仅是一个通俗的故事,也许你会发现更深刻的东西。我一直提倡一种信仰的建树,一直提倡一种人类应该具有的精神高度和道德底线。我一直想通过作品对西藏文化进行诠释,这种诠释相当于我把我发掘到的珍宝装在一个容器里,而这个容器也许是个古董,也许是个时尚。而我,将它放在了一个时尚容器里,但时尚容器里的东西未必都是玻璃球。这很有可能会是一种误解,但我必须承担这种风险。写这部作品对我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冒险。作家有时候是在冒着声誉被毁坏的风险去探索,而这种探索是值得的。
新报:这样一部作品,看得出来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你的准备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花了多久来准备?
杨志军:我是2007年完成《藏獒》三部曲的,之后我就开始着手写《伏藏》。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太多的准备,因为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多年的积淀。比如《伏藏》,它是一种被掩埋的信仰,在小说中是以仓央嘉措的情歌为密码来破解。对于仓央嘉措,我肯定是非常熟悉了,我在青藏高原生活了那么久,耳濡目染;对于《伏藏》,由于对藏文化的爱好,平时也阅读得比较多,所以不太需要做很多书案上的工作。至少,我了解这些事情。2008年写了一年,2009年改了一年。
新报:作为作者,你希望通过《伏藏》表达什么?
杨志军:简而言之,我想通过《伏藏》填补我们的精神空缺。我的后记标题是《再让我们期待一个未来》,对“填补什么空白”的问题作了解释。
“我们奔着悬疑去,但收获的是信仰的洗礼”
新报:《伏藏》有70余万字,你是否担心这个字数会影响销量?可能很多读者并不会把一本这么厚的书读完,对此你考虑过吗?
杨志军:写的时候没有考虑,但是写出来以后考虑过这个问题,当然更多的是出版社在考虑。但我必须把我的想法表达完整,我不能因为它太厚、太贵、会影响销量而减少字数。我更注重自己的表达能够给读者带来冲击。
新报:你曾经说希望通过这部作品传递“真正的西藏精神”,你所理解的“真正的西藏精神”指的是什么?是什么原因让西藏具有这种独特的精神?
杨志军:西藏精神,其实就是西藏文化的精神,也就是仓央嘉措的精神,他的精神就是佛性和人性合二为一的精神。再简化一点就是爱。宗教的最高目标是有菩提心,利他之心,爱人之心。人性和佛性的最高表现应该是统一的,都可以归结为“爱”。佛教讲人人都有佛性,这佛性说白了就是“爱”。
新报:《伏藏》被称为西藏版的《达·芬奇密码》,对于这种提法,你怎么看?
杨志军:这个提法是出版社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给读者一个很明确的第一印象。《达·芬奇密码》是悬疑故事,有阅读快感,但在这种悬疑中我们收获到的是对真理的认知。我们奔着悬疑去了,但我们收获到的是信仰的洗礼。这两本书从写作手段到写作目的,过程肯定是一致的。我读过《达·芬奇密码》,但写作的时候我考虑的是回避,我有一种超越的欲望。我必须做一种填补空白的努力,因为这是一个缺少信仰的时代。
(责编:小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