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雪域之子 > 藏韵谈话坊
专访《人文西藏》作者张鹰:每个西藏人都是艺术家

张鹰 陈度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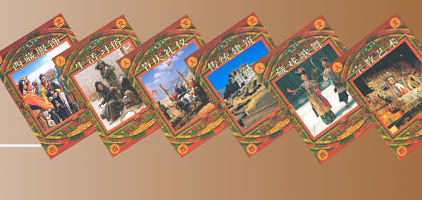
《人文西藏》丛书 (图片来源:新华网)
张鹰很像京戏里扮武生的演员平时的样子,看他精神矍铄、目光炯炯、身手矫健,好像是“练家子”、能把脚掰到脑袋顶上去。而且,和大多数武生演员一样,他也是光头。
生活中的张鹰喜欢开玩笑、喜欢恶作剧,会和年轻朋友们对一对:“白鸽白鸽,我是老鹰”一类的暗号,他往往在嬉笑怒骂中就完成了对严肃话题的探讨。
在西藏生活的37年时间里,张鹰经历过多种职业:舞台美工、民俗研究者、画油画、摄影、杂志主编……从2005年开始,他花了近4年时间,将这几十年来的民俗研究和摄影成果集结成册,于2009年5月出版了《人文西藏》丛书,集《西藏服饰》、《生活习俗》、《节庆礼仪》、《传统建筑》、《藏戏歌词》、《宗教艺术》六册。这套书被多人评为是全面了解西藏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
客厅的墙上有三幅油画,北墙上一头牛正在秋色大地上犯倔,西墙上一只牛皮船泊在夕阳下的江面上,“牛皮船”旁还挂着一幅画家陈丹青赠送的人像素描,东墙上挂的画最写实:几个牧女走在草甸上,像极具西藏风情的风光照片。黄得耀眼的色彩仿佛要从这些画框里溢出来,染得整面墙都是黄色,黄色像泼洒的灯光在屋内的空气中漫开,就满屋洋溢着金灿灿暖洋洋了。
张鹰坐在沙发上,偶尔抬头,眼光扫到这三幅画时,脸上就会透出满意的神色。
张鹰那代人的经历,就像以前有人总结过的那样:“该长身体时遇上三年自然灾害,该受教育时遇上上山下乡……”,出生于1950年的张鹰上初中时遇上“文革”,从此失学。他现在回忆起来,总会总结说:我没有正式上过大学,但西藏是培育我成才的大学。
1972年,西藏秦剧团在陕西招生,除了演员,还另招一名美工。从小喜欢画画并对美术无师自通的张鹰听说这是一份公职,而且是跟绘画相关的公职,他就去报名并通过了考试。那一年他22岁,印象中的西藏,当然不是现在人们提起的那种“大美、壮丽的雪域高原”之类的想象,那时他简直觉得如果去了西藏,也许这一辈子都不能再回家乡。但是为了能画画,他还是去了。
他们那批新招的演员和工作人员沿着青藏公路进藏,一路走一路还要慰问演出,从西安到拉萨走了22天。“但并不觉得苦,可能当时全国都苦。要知道如果在老家,以我的家庭条件和学历,想有一份跟美术相关的公职工作,那几乎不可能。”
张鹰说起他做舞台美工的经历时,语调中有一种呼之欲出的自豪情绪:“什么东西我看一次差不多就会了”。1973年,秦剧团排演大戏《智取威虎山》,进团时间不长的张鹰不知是“艺高人胆大”,还是年轻气盛,他将剧团原有的背景布全撕掉,然后重新画。那时秦剧团舞台上的灯效和布景变换都需要一帧帧先画出来,再靠人工去移动变换位置,工作异常繁杂。但也就是这一次的“壮举”,他在秦剧团的地位从此鼎立。
1974年,全国学习样板戏,当时西藏没有京剧团,就从豫剧团、话剧团、秦剧团等剧团抽调人成立了一个京剧组,让他们去北京学习样板戏《杜鹃山》,美工就抽调了张鹰。
1983年,张鹰被调往藏剧团,他现在总结时,喜欢以这一次的工作调动作为事业方向的分水岭。因为在此之前,他所做的舞台美术工作其实与西藏元素没有多大关联,他以前所接触的秦腔、京戏、样板戏等的美术设计,基本是脱离了西藏这个地域特点的独立存在,跟内地那些剧团别无二致。只有在进入藏剧团后,他才真正开始学习使用西藏元素,学习和研究西藏民俗。“是因为对藏戏的研究才渐渐转向对西藏民俗的研究”。
传统藏戏与京剧、秦腔等剧种最大的不同在于,藏戏是开放性的广场戏,没有舞台局限,在上世纪80年代,因情势所趋,藏戏开始学习其它剧种的舞台框架。
1985年,张鹰为藏戏《白玛文巴》设计舞台,为了在舞台上体现广场的感觉,他和编剧、导演商量后决定:从剧本上打破场次的概念,因为传统藏戏没有场次之分;设计上,开始采用现代戏的构成方式,采用符号化的背景。比如表现白玛文巴母亲的梦境时,整座舞台被一双佛的眼睛铺满,眼睛两边是佛的双手。但遗憾的是,很多老观众看不懂这种抽象化的设计,所以这台戏只是排演了,并没有公演过。
后来这台舞台设计参加了上海国际舞台邀请展,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就舞台美术设计来说,这种设计在当时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最重要的是,在藏剧团,张鹰的工作重心开始由舞台美术设计转向了摄影和藏戏、民俗、民间音乐研究,他经常下乡去普查藏戏的剧目和原始形态,收集民歌和各种民间艺术。这些经历为他后来做《西藏民俗》杂志主编积累了资历,也为今年他的《人文西藏》系列能成书出版提供了基础。
2002年底,张鹰调往《西藏民俗》杂志任主编,将原来的纯文字期刊改版为图文彩版杂志。2004年,他开始集中注意力编辑写作《人文西藏》系列丛书。现已成书,并被马丽华、高玉洁等人评为:全面了解西藏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
每个西藏人都是艺术家
记者: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时,西藏的艺术、文学,甚至您所从事的舞台美术设计都走在全国的前列?
张鹰:因为当时西藏艺术和文学工作者所能获得的素材来源是源源不断的,西藏能给人太多可以表述的东西,不说创造,仅仅表现好这些,就是一项大成就。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西藏生活了这么多年,在油画方面,我一直没有认真去创造过自己的风格的原因。
记者:有人说您的油画像风光照片,太写实了。
张鹰: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时,我也尝试过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尝试过一些意识形态的创作,但这几年,我还是恢复到了写实,因为我在这里生活的年数多,越来越明白西藏元素是怎么回事。我认为西藏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在我的心目中,每一位西藏人都是艺术家,能表现好他们那就是成就。在西藏,你用不着去展示自己的才华,你只需要去展示西藏共有的美,如果你能展示得好,那就是成就。
记者:您来西藏后做过的职业太多了,在每个行当都可以称为“大家”,而且据说还是首屈一指的“擦擦”研究者。您自己总结一下您的生活。
张鹰:严格说起来,我是一个“杂”家,这没什么可炫耀的,都是形势所趋,当然也有个人爱好的成分在里面。
记者:说说您的新书《人文西藏》系列。
张鹰:我在上世纪80、90年代下乡拍摄《人文西藏》书上所用的这些照片时,并没有想到以后会出书。如果当时就有了这样的意识,那我现在的这套书会更丰富一些。
我出这套书的目的,就是想向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西藏,纠正外界对西藏的误解。现在在内地和国外,仍有很多人一说到西藏就是神秘不可测。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太多把西藏神秘化的作品,猎奇和神秘甚至快成为西藏艺术的代名词,但结果怎么样呢?其作品并不能让人欣慰,真实的西藏离人们越来越远。
我们老一辈的这些人其实就是想告诉外界一个真实的西藏。
记者:您把民俗都收集到书里,注意到现在西藏的民俗已有了变化没有?甚至有些民俗已消亡。
张鹰:我已经在多处提过到这个问题,有些民俗的转变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但有些是矫枉过正。我认为西藏现在很需要一些民俗博物馆,当然这是个大话题,一言难尽。
记者:计划还出几本书?
张鹰:计划明年会出一本我的油画作品集,还会办一次画展。后年,会出一本讲述我在西藏生活的近40年时间的经历、职业变化等,名字初步定为《我的西藏,我的大学》,还计划出一本“擦擦”研究方面的书。
这都归于下一个“五年计划”了。
评《人文西藏》
由精选的三千多帧珍贵照片组成的影像画廊,和由与此相关的优美文字梳理的文化发展脉络,向世人全面系统地介绍西藏独特的人文景观和西藏文化的特殊魅力。——林继富
《人文西藏》丛书,不仅是全面了解西藏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一幅有笑有泪的生活画卷。——高玉洁
《人文西藏》既是物质文化的,也渗透着精神文化,可谓民间文化精华集大成。——马丽华
(责编:金木)







